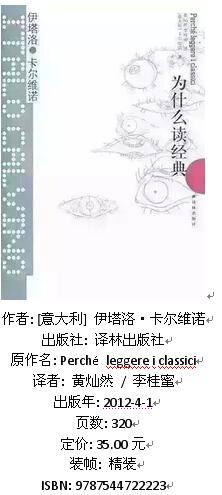选书、荐书和读书的首要原则是什么?
本站来源:微信号书入法 发布时间:2016-03-30 08:32:58 点击量:
下雨的季节
是望雨兴叹,还是冒雨前行?
不如
一盏茶,一本旧书
伴雨声雷声
重识经典
这是选书、荐书读书的首要原则
但,我们为什么读经典?

代表反复的“重”,放在动词“读”之前,对某些耻于承认未读过某些名著的人来说,可能代表着一种小小的虚伪。为了让这些人放心,只需要指出这点就够了,也即无论一个人在性格形成期阅读范围多么广泛,总还会有众多重要的作品未读。
任何人如果读过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全部作品,请举手。圣西门又如何?还有雷斯枢机主教呢?即使是十九世纪那些伟大的系列小说,通常也是提及多余读过。
在法国,他们在学校里开始读巴尔扎克,而从各种版本销量来判断,人们显然在学生时代结束很久之后还在读他。但是,如果在意大利队巴尔扎克的受欢迎程度做一次正式调查,他的排名恐怕会很低。
狄更斯在意大利的崇拜者是一小撮精英,他们一见面就开始回忆各种人物和片段,仿佛在谈论他们现实生活中认识的人。
米歇尔·布托尔多年前在美国教书时,人们老是向他问起左拉,令他烦不胜烦,因为他从未读过左拉,于是他下决心读整个《卢贡-马加尔家族》系列。他发现,它与他想象中完全是两码事“它竟是庞杂的神话系谱学和天体演化学。后来他曾在一篇精彩的文章中描述这个体系。
上述例子表明,一个人在完全成年时首次读一部伟大作品,是一种极大的乐趣,这种乐趣跟青少年时代非常不同(至于是否有更大乐趣则很难说)。在青少年时代,每一次阅读跟每一次经验一样,都会产生独特的滋味和意义;而在成熟的年龄,一个人会欣赏(或者说应该欣赏)更多的细节、层次和含义。因此我们不妨尝试以其他方式表述我们的定义:

这种青少年的阅读,可能(也许同时)具有形成性格的实际作用,原因是它们赋予我们未来的经验一种形式或形状,为这些经验提供模式,提供处理这些经验的手段,比较的措辞,把这些经验归类的方法,价值的衡量标准,美的范式这一切都继续在我们身上起作用,哪怕我们已经差不多忘记火完全忘记我们年轻时所读的那本书。
当我们在成熟时期重读这本书,我们就会重新发现那些现已构成我们内部机制的一部分衡定事物,尽管我们已回忆不起来它们从哪里来。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我们现在可以给出这样的定义:

所以,我们用动词“读”或动词“重读”也就不真的那么重要。事实上我们可以说:



如果我读卡夫卡,我就会一边认可一边抗拒“卡夫卡式的”这个形容词的合法性,因为我们老是听见他被用于指谓可以说任何事情。
如果我读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恶魔》,我就不能不思索这些书中的人物是如何一路转世投胎,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
读一部经典作品也一定令我们感到意外——当我们拿它与我们以前所想象的它相比较。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要一再推荐第一手文本,而避免二手书目,评论和其他解释。
中学和大学都应加强这样一个理念,即任何讨论另一本书的书,所说的都永远比不上被讨论的书;然而学校却倾尽全力要让学生相信恰恰相反的事情。这里广泛存在着一种价值逆转,它意味着导言、批评资料和书目像烟幕那样,被用来遮蔽文本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必须说和只能说的东西——而中间人总是宣称他们知道得比文本自身还多,因此我们可以这样下结论:

这种发现同时也是一种非常令人满足的意外。例如当我们弄清楚一个想法的来源,或它与某个文本的联系,或谁先说了,我们总有这种感觉。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定义:

这种发现同时也是一种非常令人满足的意外。例如当我们弄清楚一个想法的来源,或它与某个文本的联系,或谁先说了,我们总有这种感觉。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定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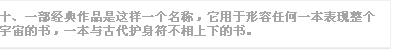
但是一部经典作品也同样可以建立一种不是认同而是反对或对立的强有力关系。
卢梭的所有思想和行动对我来说都十分亲切,但它们在我身上催发一种要抗拒他、要批评,要与他辩论的无可抑制的迫切感。
当然,这跟我觉得他的人格与我的行情难以相容这一事实有关,但是,如果这么简单的话,那么我不去读他就行了;事实是,我不能不把他看成我的作者之一。所以我要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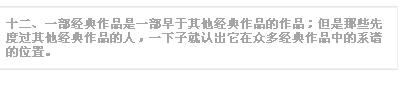
这个问题与其他问题有关,诸如:“为什么读经典,而不是读那些使我们对自己的时代有更深了解的作品?”和“我们哪里有时间和闲情去读经典?我们已被有关现在的各类印刷品的洪水淹没了。”
当然,可以假设也许存在着那种幸运的读者,他或她可以把生命中的“阅读时间”专诚献给卢克莱修、琉善、蒙田、伊拉斯谟、克维多、马洛、《方法谈》、歌德的《威廉·麦斯特》、柯勒律治、罗斯金、普鲁斯特和瓦莱里。偶尔涉猎一下紫式部或冰岛萨迦。
再假设这个人可以读上述一切而又不必写最新再版书的评论,为取得大学教席而投稿,或在最后期限极简届满时给出版商寄去作品。
如果保持这种状态而不必受任何污染,那么这个幸运者可以避免读报纸,也绝不必操心最新的长篇小说火最近的社会学调查。但是,这种严格有多大的合理性或有多大功用,尚未得知。
当代世界也许是平庸和愚蠢的,但他永远是一个脉络,我们必须置身其中,才能够顾后或瞻前。
阅读经典作品,你就得确定自己是从哪一个“位置”阅读的。否则无论是读者火文本都会很容易漂进无始无终的迷雾里。因此,我们可以说,从阅读经典中获取最大益处的人,往往是那种善于交替阅读经典和大量标准化的当代材料的人。
而这并不一定要预先假定某个人拥有和谐的内心平静:它也可能是某种不耐烦的、神经兮兮的性情的结果,某个永远都感到恼怒和不满足的人的结果。
大概最理想的办法,是把现在当作我们窗外的噪音来听,提醒我们外面的交通阻塞和天气变化,而我们则继续追随经典作品的话语,它明白而清晰地回响在我们的房间里。
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把经典作品当作房间外远方的回声来聆听已是一种成就,因为他们的房间里被现在弥漫着,仿佛是一部开着最大音量的电视机。因此我们应加上:

这反而恰恰是莱奥帕尔迪的生活环境:住在父亲的城堡(他的“父亲的家”),他得以利用父亲莫纳尔多那个令人生畏的藏书室,实行他对希腊和拉丁古籍的崇拜,并给藏书室增添了到那时为止全部意大利文学,以及所有法国文学——除了长篇小说和最新出版的作品,它们数量极少,完全是为了让妹妹消遣(“你的司汤达”是他跟保利娜谈起这位法国小说家时的用语)。莱奥帕尔迪甚至为了满足他对科学和历史著作的极端热情,而捧读绝不算“最新”的著作。读布封关于鸟类习性的著作,读丰特奈尔关于弗雷德里克·勒伊斯的木乃伊的著作,以及罗伯逊关于哥伦布的旅行的著作。
今天,像青年莱奥帕尔迪那样接受古典作品的熏陶已难以想象,尤其是他父亲莫纳尔多伯爵那样的藏书室已经解体。说解体,既是指那些古书已所剩无几,也指所有现代文学和文化的新著作大量涌现。
现在可以做的,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发明我们自己理想的经典藏书室;而我想说,其中一半应该包括我们读过并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另一半应该是我们打算读并假设可能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我们还应该把一部分空间让给意外之书和偶然发现之书。
我注意到,莱奥帕尔迪是我提到的唯一来自意大利文学的名字。这正是那个藏书室解体的结果。现在我实应重写整篇文章,以清楚地表明,经典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谁和我们所到达的位置,进而表明意大利经典对我们意大利人是不可或缺的,否则我们就无从比较外国的经典;同样地,外国经典也是不可或缺的,否则我们就无从衡量意大利的经典。
接着,我还真的应该第三次重写这篇文章,免得人们相信之所以一定要读经典是因为他们有某种用途。
唯一可以列举出来他们欢心的理由是,读经典总比不读好。
如果有谁反对说,它们不值得那么费劲,我想援引乔兰(不是一位经典作家,至少还不是一位经典作家,却是一个现在才被译成意大利文的当代思想家):“当毒药正在准备中的时候,苏格拉底正在用长笛练习一支曲调。‘这有什么用呢?’有人问他。‘至少我死前可以学习这支曲调。’
1981年黄灿然 译